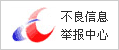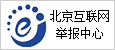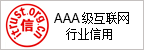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 吴怡
教育法治化的核心价值绝非形式上的“有法可依”,而在于通过良法善治切实保障教育场域中每一个体——尤其是学生与教师——的基本权利与尊严。受教育权、学习权、发展权、学术自由等基本权利的充分尊重与有效实现,以及受损权利获得及时公正的救济,是教育法治的灵魂与终极目标。以权利保障为价值原点、以救济机制为实践支撑,是教育法治化纵深发展的核心进路。
一、权利保障:教育法治化的价值基石
权利保障的优先地位源于教育的本质属性和法治的核心精神。
教育的内在诉求:受教育权(《宪法》第46条)和学习权是学生发展的根基;学术自由(《高等教育法》第10条)是教师探索真理的前提。脱离权利保护,教育法治易沦为管控工具。
法治的核心回归:法治在于“规范公权,保障私权”。教育领域庞大的行政与管理权力(招生、学位、职称、校管)需受法律约束,根本目的正是防止权力滥用,保障教育公平正义。将权利保障置于核心,是对“法治为民”本质的回归。
破解现实困境的关键:入学不平等、惩戒失范、学术自主受干预、申诉不畅等问题的根源,常在于权利边界模糊、保障缺位。唯有确立权利保障为首要目标,才能扭转“重管理轻权利”惯性。
权利保障构成教育法治化的价值基石与逻辑起点,为制度构建提供终极标准。
二、实践挑战:权利保障与救济的现存短板
当前教育法治在权利保障与救济层面面临严峻挑战:
1. 立法层面:
权利界定笼统:现有法规对“受教育权”、“学术自由”等规定原则抽象,内涵外延不清,义务主体不明。
程序保障缺位:涉及师生重大权益事项(开除、学位撤销、解聘、学术评价)缺乏统一刚性程序规范(告知、申辩、听证、说理),“重实体、轻程序”明显。
新兴权利滞后:学习数据隐私、在线教育权益、AI教育公平等新兴诉求,立法保护存在空白。
2. 执法与治理层面:
权力运行失范:部分教育行政部门或学校裁量权过大、决策不透明,存在不合理设限、选择性执法等侵权现象。
学校治理失衡:学校章程“权利保障”条款薄弱虚置。师生参与权、表达权、监督权未有效落实,管理本位思维主导。
权利意识薄弱:管理者、师生自身权利意识不强,或不知权利、或不敢主张,形成权利实现的隐形障碍。
3. 救济层面:
校内申诉虚置:申诉委员会独立性差(管理者主导)、代表性不足、程序不规范(无听证、不说理)、结果约束力弱。
行政救济弱化:教育行政复议受理范围窄、审查标准轻合理性、机构中立性存疑、决定执行力不足。
司法救济困难:教育纠纷常被以“高校自主权”或“内部管理行为”为由拒之门外。受理后也面临专业理解局限、周期长、成本高难题。
替代机制匮乏:专业教育仲裁机构空白,教育申诉专员制度缺失,行业社会调解作用有限。
这些短板相互交织,形成制约权利实现的现实藩篱。
三、实践进路:构建权利保障为核心的教育法治生态
推进教育法治化,须以权利保障与救济为主线,多维度协同发力:
1. 完善立法:构建清晰可操作的规则体系
细化权利清单:推动《教育法典》编纂或修法,清晰列举学生(学习选择权、公正评价权、人格尊严权、参与管理权、数据隐私权)和教师(教学自主权、学术自由权、职业发展权、民主管理权)核心权利及其边界。
强化程序正义:法律确立重大权益事项(处罚、评价、资源分配)的最低程序标准:事先告知、陈述申辩、重大事项听证、回避、说明理由(书面)、及时送达。将程序合规作为合法性刚性要求。
填补新兴空白:加快制定在线教育、教育数据安全与隐私、AI教育伦理等法规,保护新型权益。
2. 规范权力:推动治理法治化转型
厘清权力边界:通过权力清单、责任清单明确职权范围与行使条件,压缩裁量空间,落实“法无授权不可为”。
深化依法治校:强化章程的“权利保障”内核与执行力。章程制定修订保障师生实质参与。明确校务会、学术委员会、教代会、学代会等在保障各自群体权益中的法定地位、职权与规则。
推行执法规范化:在教育执法中全面落实行政执法公示、全过程记录、重大决定法制审核“三项制度”。
培育权利文化:将法治与权利教育融入校长教师培训及学校课程,提升管理者法治思维与师生维权能力。
3. 畅通救济:构建多元协同的救济网络
重塑校内申诉:法律强制设立独立、公正、专业的申诉委员会(含校外专家及合理比例师生代表),规范程序(保障听证、知情、获助权),赋予决定强约束力,衔接复议诉讼。
改革教育行政复议:
扩大受案范围:纳入更多重大学校管理行为(学位、纪律处分、职称程序)。
提升专业独立:探索设立相对独立、专业化的复议机构。
强化审查深度:兼顾合法性与合理性审查(比例原则、正当程序)。
增强决定效力:明确其强制执行性。
完善司法救济:
扩大受案范围:明确将开除、不予注册、学位撤销、教师解聘等纳入行政诉讼。
设立专业审判机制:探索教育审判庭/合议庭或专家陪审员制度。
优化审查标准:在尊重学术规律前提下,明确对程序合法性、事实基础、法律适用的审查。
发展替代性机制(ADR):
建立教育仲裁:推动设立独立专业仲裁机构,提供高效低成本解纷途径。
推广专业调解:支持教育行业组织设立调解中心化解学术争议、校园伤害等纠纷。
引入申诉专员制度:试点设立教育申诉专员作为独立第三方调查投诉、促进和解。
教育法治的生命力在于对人之尊严与权利的深切关照与有力捍卫。将权利保障与救济置于核心,是回归教育本真、践行法治精神的必然要求。这要求超越“管理便利”思维,在立法中勾勒权利图谱,在执法中恪守权力边界,在治理中激活主体参与,在救济中铺设多元正义之路。唯有构建以权利为基石、救济为支撑的法治化教育生态,方能实现“办人民满意教育”的承诺,让每个教育参与者在法治阳光下有尊严地学习、探索与成长。这是教育现代化的内核,亦是法治中国在教育领域的生动实践。